长久以来,人们的头脑中似乎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听话的员工才是忠诚的员工。因为“听话”,他们的行为中规中矩,极其符合领导和上司意愿。行为服从成为员工“忠诚”的代名词和突出表现。对于那些行为奇特、难以实现服从的员工,管理者多以“叛逆”之名对之。
然而,行为服从真的就能代表员工“忠诚”吗?根据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乔西亚·洛伊斯的观点:“忠诚自有一个等级体系,也分档次级别。处于底层的是对个体的忠诚,而后是对团体,而位于顶端的是对一系列价值和原则的全身心奉献”。行为服从是一种明确的表面状态,这种表层次的“忠诚”反映的恰恰是员工对企业活动的漠不关心。
行为上过度的服从难免会增加管理层决策的难度,如果不论领导说什么,都不顾实际情况坚决执行,其必然导致决策“浪漫化”、“主观化”等问题的出现。这种表层上对个体行为的服从,恰恰反映了员工高层次上的不“忠诚”。以“行为服从”论“忠诚”的观念就成为了员工忠诚的“一大悖论”。
真正高层次的员工忠诚应该体现在员工以企业利益为主的全方位考虑中,这种高层次的员工忠诚才是现代社会保持组织优势的根本基础。王石的接班人郁亮曾经用一句话表示他对王石意见的反应:“执行董事长的话要过夜。”通常他在对王石的意见说考虑研究时,就代表有不同的想法。执行董事长的指示一定要过夜,过了夜想想再执行或者不执行。
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想法不一样确实很容易导致分道扬镳。思维是员工思考问题的方式和侧重的路径,如果员工的思维相去甚远,行动中的冲突在所难免,这时要实现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似乎是天方夜谭。
然而,事实上,员工为了得到更好的发展,通常愿意同与自己有差异的人一起工作,实现互补。而且,企业中聚集大批思维相似的员工,必然导致企业发展中遭遇“盲点”。如果所有员工都“心细如发”,关心细节问题,那么企业发展中的宏观趋势问题又有谁来把握呢?何况一旦企业内部大部分员工达到了一种“思维趋同”的状态,企业的个性和创新性就会受到遏制,一个失去创新能力的企业根本就谈不上持续发展。将员工“忠诚”等同于“思维趋同”,无异于舍本逐末,这已成为员工“忠诚”的第二大悖论。
企业要发展,必须重视员工差异的价值,员工的“忠诚”绝不能建立在“思维趋同”的基础之上。盛田昭夫在任索尼公司副总裁时,田岛道治为董事长,两人常有不同意见,田岛道治想要离开。对此,盛田昭夫坦诚表态:“如果你发现我们在一切问题上的意见均一致,那么这家公司确实没有必要给我们两个人发薪水。这种情况下,不是你就是我必须辞职。正是因为我们有不同意见,这个公司才会少犯错误。”
古语有云:道不同,不相为谋。诚然,价值观上差异的存在会对员工“忠诚”产生致命的影响。价值观反映的是员工目标和利益,没有相同的利益和目标,很难想象员工“忠诚”从何而来。员工“忠诚”必然要仰赖于价值认同这一核心,戴尔公司的创始人迈克尔·戴尔认为:无论聘用的是新进人员,或是负责经营最大事业体的管理阶层,都必须与公司的哲学和目标一致。如果这个人可以认同公司的价值观和信念,也了解公司目前的营运和努力方向,那么他不但会努力达到眼前的目标,也会对组织的最大目标有所贡献。
但是,反过来说却未必尽然。价值认同并不是保证员工“忠诚”的充分条件,只是必要条件之一。价值观也是在一定物质基础上形成的,人不能只依靠观念生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在拥有价值认同的基础上还必须具备相应的物质保障。美国管理学家拉伯福指出:“人们会去做受到奖励的事情。”也就是说,单单价值观上的认同并不足以形成员工“忠诚”,企业必须通过一系列的激励措施实现员工的“忠诚”。简单地将“价值认同”等同于实现员工“忠诚”,可能导致对相关价值激励措施的忽视,难以构建满意的员工“忠诚”度。
弗雷德里克认为:忠诚是忠于某个企业据以长期服务于所有成员的各项原则。一旦曾经为之奋斗的“原则”不存在了,员工就可以主动选择离开。从本质上说,员工“忠诚”是一种忠诚于优秀的工作态度。员工遵守与企业的劳动合同中的各种承诺和约束,在合同有效期内为企业服务,并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与员工都是独立的个体。个体员工无法决定或是改变企业的经营方针和战略。企业有招工的权利,员工也有选择企业的权利。随着企业的发展,其原有的价值观和文化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一旦企业出现个体员工无法接受的价值因素,员工的流动无疑对双方都有利。如果员工一方面在职期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能够为企业的兴旺尽职尽责;另一方面,离职后,在一定时期内能保守原企业的商业秘密,不从事有损原企业利益的行为,这丝毫无损于员工“忠诚”。
事实上,这样的实例比比皆是。惠普公司的人员流动就比较大,在新招来的员工中,5年后,大概只有50%的人留下,10年后,只有25%的人留下。然而,留下来的人肯定对惠普文化坚信不移,行为举止也是惠普化的,这样的人肯定会帮助惠普做出很多有益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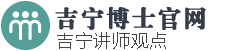 吉宁博士观点
吉宁博士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