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籍建筑师奥雷舍人在中国、新加坡、泰国主持设计了多处地标性建筑比如与库哈斯合作的位于北京CBD的CCTV大楼。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他试着将自己融入进去,同时坚持自己对建筑的理解。面对质疑与指责,他认为,如果没有争议,“只能说明你的设计没有任何新意”。
HBRC:你如何走上了建筑师之路?
奥雷舍人:出生时,我的父亲还是一名建筑系大学生,于是我对建筑从小就耳濡目染,也曾在父亲的办公室工作。但到了18岁,我的心思扑在音乐上,认为自己与建筑无缘。我搞了一辆小汽车,四处旅行。旅行让我从根本上重新认识了建筑。
比如,有一次我行走在瑞士的意大利语区,被那里的房屋吸引,溜进了一栋私宅,房屋的主人没有对我发火,还向我讲述了这栋建筑如何改变了她的生活、改变了她对建筑的理解。这件事让我明白,建筑不只是物体本身,还包括它如何对人产生影响。如果你想要理解它,就一定要看到它、走进它、感受它。显然,我的确热爱建筑,到现在仍觉得这是一条非常值得走下去的路。
HBRC:不仅在中国,你在亚洲其他地方设计的一些建筑也成为地标性建筑,在你看来,你的作品能够在亚洲受到欢迎的原因是什么?
奥雷舍人:我所期待的就是塑造“混血儿”,将东西方的哲学与文化结合起来。而我并不像一个典型意义上的西方人那样,生长在西方,将西方的东西搬过来。我想要工作在亚洲、生活在亚洲、接近亚洲、成为亚洲的一部分。
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找到新的元素,新的视角,而不是重复前人所做过的事。比如,摩天大楼是典型的西方产物,而如今亚洲遍地都是摩天大楼,但所有的摩天大楼几乎都是一样的,笔直向上,高耸入云。为什么我们不根据每个地方的特点和人们的需要做出一些改变?我关注生活在其中的人如何利用这些建筑,如何看待它们,这些建筑为公众做了什么。
建筑应表达对公众的关注,这是建筑师们的责任。我对单纯建造看起来与众不同的东西没有兴趣。我设计建筑时,并不追求奇特外形,而对功能和理念的不同思考会最终形成不同的外形。外形是建筑意义的产物。
HBRC:在北京建立自己的建筑事务所,与之前担任雷姆库哈斯的合伙人是否非常不同?
奥雷舍人:是的,我要创立的是一家始于中国、成长于中国的建筑事务所。它不是将欧洲的设计带到中国,而是在中国酝酿生产设计。运营一家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工作很复杂,不论你怎样做都无法让它变得简单。你必须处理技术问题,应对技术专家,依据建设的实际进展规划工作;同时所有的一切必须与文化、哲学等背景相吻合;还要从心理学的视角考虑人们如何感知;建筑项目常与政治相关,有时要代表一座城市,因此你还要应对媒体和公众,应对来自每个人的不同观点。中国正处于挑战和机遇之中,这带来对未来的思考,带来尝试一些可能性的机会。
HBRC:你现在以北京为中心开展工作,并且拥有三分之一的中国员工,如何在工作中处理文化上的差异?
奥雷舍人:我离开德国已经二十年了,在某种意义上,我是德国人,但在另一层面,我已不再是典型的德国人。我曾在八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生活过,在不同的文化之间穿行对我而言已经成为一种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对我来说,交流对话是我一直感兴趣并寻找的,面对文化差异并不容易,但却非常有趣,非常有意义。但坦白讲,我不太相信“关系”这回事,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想法单纯,甚至有些幼稚。我只是想要我的作品本身卓尔不群。我相信我的作品的质量,相信我们所做的改变的重要性,没有任何其他事务能凌驾其上。
HBRC:你辗转于各地,私生活也非常吸引眼球,你如何在庞杂的事务中保持专注和严谨?
奥雷舍人:我的生活一直非常紧张,频繁旅行,工作繁多,需要找到自己的节奏。我早上醒来会想今天一天的任务,因为人在早上还没有被事务所打扰,能够非常清醒地为事务排出优先级。而我只要一到公司,就有约50人要和我谈,几百封邮件要处理。
在事情一下子全部涌过来的时候,排出优先级非常重要。要试着聚焦于整体蓝图和战略决策,然后投身于细节。所有的细节对于建筑来说非常重要。建筑就是一个将不同层面细节与不同层面的战略相结合的工作。如果你热爱建筑,那么工作实际上并不会成为一件消耗你能量的事情,相反,它能够不断激发你的能量。
HBRC:如何看待自己的建筑设计所引发的争议?
奥雷舍人:在我的工作中,争议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当你做出一些真正的新东西,很难做到让所有人立刻接受它。如果所有人都第一时间接受了你做的东西,那只能说明,你所做的没有任何新意。
对新事物的理解,是一个过程。CCTV大楼就是这样。建筑设计是为了使用,而不是矗立在那供人看,我相信在CCTV大楼对公众开放后,人们会慢慢理解它。如今世界上最知名的建筑,埃菲尔铁塔和悉尼歌剧院,建立之初曾遭到很多人的憎恶。超前的事物总是难以令人接受的。因此,我们的工作总是伴随着争议。至少,CCTV大楼已经引发人们的思考和质疑,保持思想的流动是一件好事,即使人们给它起一个好笑的名字,我也完全不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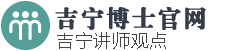 吉宁博士观点
吉宁博士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