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民营企业家改革作为企业为什么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难道民营企业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看看一些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如红塔山、长虹、海尔等你不又能说他们不是真正的企业。但研究这些企业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海尔这些民营企业家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家了。他们虽是公有,但并不是国家原来重点投资兴建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了,而国家初始意义上所谓的重点骨干企业,据统计大多已名不副实了,相反倒成了国家的包袱。现在人们能随口叫得出名字的好企业大多是自己从市场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如前面提到的企业。他们一般都是由小企业变成大企业的(有例外的只是一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企业如中石化、中国电信等)。
一、企业理论简史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企业发展的历史。
手工作坊式的家族企业代表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代表则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托拉斯等形式的垄断企业则代表着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现代跨国公司的兴起和企业形式的多样化则代表了现今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理论孕育于实践,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企业的变迁同样也带来了人们对企业的研究——企业理论的发展。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讲,企业理论的历史与企业的历史、资本主义的历史一样悠久。所以有的经济学家又称之为“‘黑箱’企业理论”。现代企业理论的发端源于罗纳德·科斯在1937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在该文中科斯第一次用边际替代的分析工具,研究了企业产生的原因,认为企业之多以能代替市场是因为“发现”市场价格需要成本,而取代市场的企业正式节约了这种成本。
当然,以上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各种理论往往相互交叉。同时,这些理论又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假定企业存在于签约自由的市场环境,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企业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的私有产权基础之上,并且这些理论也都重视产权作用,可以说现代企业理论或多或少受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因此,在中国还没有彻底完成产权改革以前,研究中国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家改革往往存在理论瓶颈,于是国内很多学者就试图通过对企业机制的设计来规避这一“瓶颈”,但效果往往不佳。本文也想作这方面的尝试。
二、民营企业家改革悖论的解释在简要回顾了企业理论的历史现状后,让我们再回到我国的民营企业家问题上来。
不妨再问一次,民营企业家改革到底要不要该不该追求利润最大化,还是,民营企业家改革就应该是少数关系国计民生、产品“公共特征”明显的、私人企业不愿投资的行业企业退一步讲,就算是承认民营企业家改革有其极大的公共性、社会性,是些微利甚至不盈利的行业企业,问题是现在全国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家改革显然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无法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对此,国内许多学者纷纷提出了对策,最终大家意见比较一致并影响了中央决策的是民营企业家战略性重组论。但是尽管在民营企业家改革战略性重组或大调整这一大方向上取得了较一致的观点,但是大家对于怎样实施民营企业家大调整,调整到什么程度等具体问题上分歧很大。比如有的学者从产权特性和产业定位的角度出发,认为共有产权对应的产业定位是非(弱)竞争性、非(弱)盈利性的行业,而私有产权者相反。但问题是很难划分何为非(弱)竞争性、非(弱)盈利性的行业,何为竞争性、盈利性的行业。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随着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原来由企业直接经营或私人公司特许经营的公用事业,如电力、电信、煤气天然气、航空运输等,正由垄断行业变为竞争性行业。世界在变,我们很难为民营企业家规定应该经营什么。那么关键在哪呢?我认为是出在民营企业家改革悖论上,解决了这个悖论答案也就水落石出了。众所周知,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自觉不自觉)地朝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中国以前的经济不是市场经济,而是一种中央命令型的经济。“企业热心办企业,认真管企业,本身就象一个大企业”。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不存在产权独立、边界合理,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于是整个中国就用一个“企业”替代了整个市场,“整个经济成了一个大工厂”,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由企业部门把握,资源靠行政指令配置,一切行为在统一计划和指令下完成,人们没有任何选择权,除了婚姻自由(甚至连婚姻自由在实际上也受到了限制)。
显然,这种替代决不同于科斯在论述企业产生时的那种“企业代替市场”。因为这种替代不存在边界。在1937年的论文中,科斯曾提出过两个假设:一个假设(为了某些目的做出的)是,资源的配置由价格机制决定;另一个假设是(为了其他一些目的做出的)是,资源配置依赖于作为协调者的企业家。”企业之所以能代替市场,原因就在于在企业中企业家的协调或权威能够节约交易成本,企业也不可能无限的替代是市场,因为企业存在自身特点所决定的边界。企业的边界就是,在边际上由企业组织带来的交易费用等于由市场配置资源带来的交易成本相等这一点。共产主义国家作为一个“超级企业”,并不是因为在边界上他能够完全代替市场,而是政治的需要,是一种理性设计的结果。而“超级企业”一旦建立,原先存在的各种市场交易活动就一律内化成了企业的组织活动,“价高者得”的市场价格机制完全消失,各级等级机构(通过官员)的“看得见的手”的监督指挥成了取代混乱的唯一选择。民营企业家则正是这一大工厂中一个个车间或工作组,民营企业家顶多只是有了企业的形而没有企业的神,即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以及形成这一机制所必需的权能结构和外部市场环境。民营企业家改革的悖论正是源于此。如果没有改革,没有引入市场机制,那么民营企业家原有的一套机制则是可选择中方案中的最优方案。问题恰恰是改革了,在新的市场环境下,民营企业家可选择的行为方式增多了,从而原有的“超级企业”机制无法再在可以承受的交易成本范围内对企业进行约束,而这种被动的“放权”又进一步导致了民营企业家改革行为的多样化:道德败坏和机会主义盛行。问题的关键在于民营企业家改革没有对市场机制的变革作出相应调整和改革。可以说在企业的治理结构上,改革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民营企业家与原来作为“超级企业”中的一个单位的民营企业家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当然全国各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做的好一些,比如广东、浙江等,而有些地方则做的差一些,比如中西部、东北等)。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据调查广东省的大型民营企业家的经理任命权大部分仍旧掌握在各级地方企业手中,因此民营企业家改革的治理结构在激励机制这一点上,行政组织成了对经理实行强激励的主体,而企业作为另一个组织却成了弱激励主体,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这么可能追求利润最大化呢?现在我们假定交易成本为零,并且“超级企业”已经成功的替代了整个中国市场,同时我们也不去讨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怎么会产生超级企业替代市场的动力机制。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超级企业能够在政治家(另一种意义上的企业家)的组织协调下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当然这种假定不符合现实,需要修正,交易成本一般为正。事实上“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也许很高,尤其是当许多不同活动集中在单个组织的控制下时更是如此。”而且这种成本并不总是成比例的随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增加,通常是无规则的跳跃上升,所以很难控制。中国由于特殊的时代形成了特殊的政治家(企业家),相对来说,那时的组织协调成本较低,一定程度上这与d·诺斯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有关,因此超级企业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基本实现(尽管代价很大,但却是当时情况下的最优选择)。随着意识形态的乱用,超级企业的运转也随着“政治家”的“衰弱”而陷入“瘫痪状态”,效率很低,资源浪费惊人。所以改革最初面对的就是瘫痪了的超级企业,目的是把市场的权力还给市场,让民营企业家改革成为真正的企业。探究超级企业失败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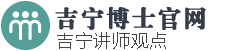 吉宁博士观点
吉宁博士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