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郭重庆院士认为,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办学至今才短短20多年,但已经走过了学习、借鉴、模仿、从文本到文本、写读书报告的阶段,现在面临着后20年的路如何走的问题。
郭重庆认为,中国管理学应模仿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发展思路的表述,从对外来管理文化“照着讲”的阶段,走向“接着讲”的阶段;管理思想根植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之中,因此必须本土化。
那么,中国本土管理思想是否存在?它对现实中国的管理是否有指导作用?它能否形成一门独特的中国本土管理学?
非主流的“管理学元问题”
刘人怀等提出了管理学需要反思的23个问题,其中包括:什么是管理?什么是管理活动?什么是管理者?管理与management、adMINIstration等的差异是什么?……提出要对management、administration、science、management science做一番正本清源的探讨,甚至建议要把“管理”的汉语拼音guanli向世界(包括英语世界)推出,将管理科学翻译为guanli science(GS)。
借鉴“元科学”、“元社会学”等概念,可以将这些有关管理与管理学发展密切相关的根本性问题称之为“管理学的元问题”。
事实上,这些管理学以及中国本土管理学在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根本性问题,很难在当今管理学主流研究范式中得到圆满解答,因为相当多争论已进入哲学层面,此类问题本身就处于主流管理学的问题域之外。例如,“管理”是不是“学”?到底应该称之为“管理学”还是“管理科学”?
管理学主流范式的要点主要包括:①不讨论抽象的管理本质问题,而着重讨论作为工具和手段的管理;②重视管理的科学性方面,管理学主流刊物和正规的管理学学术教育通常并不讨论管理的艺术性,而实际上管理的艺术性是非常重要的;③通常采用实证的方法解决管理学问题。而管理学的元问题则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①关于管理的本质问题;②关于管理学的理论性质问题;③关于管理学研究方法论问题。两相对照即可发现,管理学的元问题是无法在管理学的主流范式框架中得到解答的。
管理学主流研究并不是没有认识到“元问题”在管理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而是在其实证主义范式框架中根本没有办法讨论管理的本质问题,因为管理的本质涉及管理的价值理性,人们容易使用实证方法检验某种价值观下的行为方式,但很难理解和评价这种价值观本身的历史及其变化。
劳动永远是社会的劳动,人类为了有效抵御自然,向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就必须共同劳动,结成一个集体,而集体总是要有组织、有秩序、有分工,也就需要管理。如果没有管理,没有维系一定的秩序和原则,没有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劳动是不可能的,因此,管理与人类存在方式是同一的,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管理史。或者说,管理本身就渗透了人类对于自身如何存在的理念。既然如此,管理就必然包含其价值维度。在经济学家看来,管理是生产劳动的一个条件,没有管理就没有生产,管理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在社会学家看来,管理是一种职权系统,透过管理,社会形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角色分工;在政治学家看来,管理可能是一个阶级、地位或权力,它同社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相联系。 管理的“效果”既然是对于人而言“有用”,那么它对于什么人“有用”?这种“有用”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对于人类的最终幸福有何影响?
显然,以上管理价值论的内容是在管理学的主流研究问题域之外的,因为管理学主流研究持有典型的管理工具论立场。尽管管理学主流学者声称管理在于其“效果”和“效率”,但迄今为止著名的管理学家中,很少有人对“效果”作了定义或直接将其简化为企业的经济绩效。泰罗的定义是: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同时也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法约尔将管理演变为一种纯粹的工具论—管理就是实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这是一种纯粹的工具论和手段论的定义。孔茨认为,管理是在正式组织中,通过或与人完成任务的艺术,它是在组织中创造环境的艺术,是在组织中能够以个人和合作的方式完成组织目标的艺术,是在完成这些工作中消除障碍的艺术,是在有效达到目标时获取最高效率的艺术。尽管孔茨对管理的定义较为复杂,但定义中“组织目标”究竟为何,并没有说明。德鲁克则基本上将其等同于经济绩效。罗宾斯认为,管理是指同别人一起,或通过别人使活动完成得更有效的过程—这一经典教科书的定义同样没有明确组织究竟应该追求何种效果。
管理的本体价值:关乎人的信仰
撇开管理的本质问题,将管理视为一种工具,就不会存在所谓的中国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别;管理根本上就是同质的、就是中性的。而事实上,管理恰恰不是一种中性的存在。管理包含着管理目的的确立,其确立依赖于主体现有的观念以及主体对未来的理想结果所作的预见和推测,而这种理想结果在管理活动实施之前还没有实现,因此,管理的目的是人性理想与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国、各民族的不同管理方式正体现了其不同的人性理想与文化本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如果将建筑仅仅视为一种工具,则我们就永远无法理解建筑的实质。与此类似,如果仅仅将管理理解为工具,则我们也将永远无法把握管理的实质,从而也无法把握中国本土管理学的实质。
进一步来说,人的本性是在管理中实现的,管理及其理念代表了人类作为社会性存在的本质,正是管理构建了人类世界。人类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本质上是一种为了更好地协调社会活动而形成的管理结构,抽离其中的管理实质,人类社会将变成一盘散沙,因此,管理构建了人类社会。将管理与人类的存在方式联系起来意味着,如何理解人类的存在就会如何理解管理,而反过来,有怎样的人类理想,就有怎样的管理理念。从这个基础上来看,中国本土管理思想一定是存在的,它有别于西方管理,也只有把握这个基础,才能进一步研究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实的中国管理是否有指导作用,以及能否形成一门独特的中国本土管理学的问题。抛弃这一基础,将管理视为纯粹的工具和中性的存在,就绝不会有中国本土管理学,正如不可能会有中国物理学与中国生物学一样。
管理本体论是解答中国本土管理学元问题的一条可能途径,管理本体论以深入研究管理的本质问题为其要义。事实上管理学主流范式也有其本体论—在管理学主流学者看来,管理的本体就是工具论的本体,管理的价值就是其工具价值。与之相对,我认为,管理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方式,必定寄寓了人们实现生存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即一种合适于人性理想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协调方式。管理的本体价值是自足的,它与效用无关,而关乎人类的信仰与文化本质。
这种本体价值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为人们所信奉,并给他们以族类认同和情感慰藉,如中国古代的儒家管理思想以及儒家价值观下人与人的协调关系。笔者不揣冒昧地认为,管理本体价值才是解开一切有关中国本土管理与中国本土管理学问题的真正钥匙。
走出“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陷阱
中国文化和现代生活并不是两个截然不同而且相互对立的实体。余英时指出,所谓普遍性的“现代生活”和普遍性的“文化”一样,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是找不到的。 现实世界中只有一个个具体的现代生活,如中国的、美国的或日本的,而这些具体的现代生活都是具体的文化在现代的发展和表现。事实上,社会科学家关于“现代化”的无数讨论主要都是在寻求共同的特征,也就是理想的典型,但是典型如果要使用于一切具体的、个别的现代社会,势必不能通过最高度的概括,其结果则是流为一些空洞的形式,而失去了经验的内容。由此,中国当代管理与传统管理思想也不是相互对立的。从管理的本体价值来看,中国当代管理没有办法彻底抛弃其历史延续的价值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罗家德教授就认为,尽管不断受到西方管理思想的影响,但是中国的管理组织仍然反映了相当强的传统特质,主要体现为三点:①我们的组织是网络式的;②我们的组织仍然保持关系社会、人情社会的特质;③我们的领导仍要情、理、法兼顾,保有礼治秩序的特色。综上,管理一定是民族的、历史的、演化的,是传统与现实相融合的,不直面传统,就不可能直面现实;不直面现实,也无法直面传统。
管理本体不仅体现传统与现实的融合,也体现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的融合。自法约尔将管理学工具化以后,主流管理一直以来秉持的是工具价值至上的立场。工具价值是指对于其他事物来说仅仅作为一种工具的那种价值,正如本文前述,经典管理学家尽管也提到管理的“效果”和“目的”,但他们本质上关心的是手段,很少关注目的本身是否合理。就工具价值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能够找到解决事情的方法、途径,它最大的兴趣在于选择最优方案、决策和手段,它关心技术上的可操作性。
相对而言,本体价值是一种最终价值,是一种内在的价值。霍克海姆等认为,内在的价值的焦点“在于一种与至高的善的思想有关的概念,一种与人的规定性以及如何实现最高目标的方式的问题有关的概念。它是实在固有的一个原则,是一种生活方式,即一种与生命、自然谋求和谐的方式,它提出了一个‘真理的’和谐世界的可能性”。人们可以这样认为,“内在好之物不是派生出来的好,它本身就是好。如果不是内在好之物,那么它就是派生出来的好,它之所以是好的,不是因为自己本身就是好,而是因为其他事物的好,且它以某种方式与该其他事物有关的好。”
综上所述,中国管理实践不同于西方之处,主要是其本体价值的不同,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形成的人文理想在管理中的体现。不从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融合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管理实践的内涵,将永远不会找到中国本土管理学登堂入室的门径;同样,不从传统与现实融合的角度考察中国管理实践的内涵,“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究竟有用没用”也将只会永远停留在“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陷阱中无法自拔。
相关推荐:
杭州网络营销策划
杭州企业管理咨询
组织管理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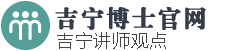 吉宁博士观点
吉宁博士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