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利斯”袭来,洪水围困广东省坪石监狱四大队关押点,围墙垮塌,监舍进水,洪水将1663名服刑人员“驱赶”到一处高地形成的“孤岛”。
危急时刻,有关部门紧急应对,作出大转移的决定。
70多名监狱警察和30多名武装警察,带领服刑人员跋山涉水,“刀劈手砍,开出一条山路”,开始了我国监狱系统最大规模的服刑人员紧急转移。至转移结束,1663名服刑人员无一脱逃、伤亡。
“碧利斯”检验着受灾地区应急管理能力,坪石监狱的这次成功大转移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同时“应考”的还有受“碧利斯”影响,发生严重洪涝灾害的湖南、福建、广西、江西、浙江等省(区)。
浙江省不仅海岸线既长又“暴露”,而且“碧利斯”来临时正逢天文较大潮期。然而,如此之大的灾情,却只造成这个省近7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还不到去年“泰利”台风受灾损失的十分之一;全省截至目前更是未接到1名人员伤亡的报告。
据了解,“碧利斯”来袭之前浙江全省提早就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碧利斯’在浙江未酿大灾,与浙江‘预’的早,与中国应急管理有力是分不开的。”有媒体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突发事件高危时期到来催生应急机制从无到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种认识自古就有。应对突发事件,也不是从现在开始的,而是自古就有。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来都没有形成一套成文的、自成体系的整体预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彭宗超说。
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目前已“进入突发公共事件高危期”,“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都将面临突发公共事件所带来的严峻考验”。
“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影响并不仅止于人员伤亡、经济损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研究基地研究员顾林生说,事故灾害发生之后,枯燥的伤亡数字背后往往是一个个家庭悲剧。不仅公众的生活节奏被打乱,公众心理也会受到巨大冲击。
作为研究危机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学者,彭宗超对危机中国应急管理机制的形成历程十分熟悉。他介绍说,正是一系列重大灾害事件的发生,让各级企业从沉痛的教训中,逐渐认识到自己处理突发事件的意识缺位和能力不足。
于是,2002年5月,广西南宁市应急联动系统正式运行,成为中国最早成立中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城市。
2003年年初,上海市编制完成《上海市灾害事故紧急处置总体预案》,这是省级企业中最早编制的应对灾害事故的预案。
然而,“这些常规化的日常管理机构”,以及“各个城市的单打独斗”,在真正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仍存在很多不足”。
灾难不会因为人们的准备不足而不再降临。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威胁着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在疫情初发阶段,“应急准备不充分,信息渠道不畅通”等缺陷被充分暴露。
在付出高昂代价的同时,企业高层切身感受到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的重要与紧迫。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成为中央企业日程表里的重要内容,“应急预案”也从一个比较陌生的词语逐渐变成了老百姓的流行语。
令人兴奋的是,面对疫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应时而生,防治非典的被动局面开始逐步得到扭转。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局有关研究人员将成功抗击非典,看成是“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综合化的转折点”。
此后,国家开始启动总体应急预案的编制工作,各地方、各级企业也把各自应急预案的制定提上日程。
2003年7月,国家提出加快突发公共事件中国应急管理机制建设的重大课题,国务院办公厅专门成立“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工作小组”。从此,中国应急管理机制的建设全面提速,走上了快车道。
2003年9月,《北京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应急预案》公布。
同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提升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
2004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将《省(区、市)人民企业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框架指南》印发各省,要求各省人民企业编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2004年9月,“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提升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进一步明确提出。
2005年1月,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25件专项预案、80件部门预案,共计106件。
2005年7月22至2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此次会议被誉为“中国应急管理纳入经常化、制度化、法制化的工作轨道”的一个标志。
就在全国各地加紧建设应急管理机制之时,灾难再次来临。2005年秋冬,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降临。
但与非典疫情肆虐时相比,此次疫情的发生并未使民众惊慌失措。也就在此时,国务院第113次常务会议通过《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这一切都表明,我国企业应对公共危机的管理能力已得到明显增强。”专家们认为。
伴随着考验,应急管理机制的建设步伐稳步向前。
2006年1月6日,国务院发布《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1月8日,国务院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此时,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已编制了国家专项预案和部门预案;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均已编制完成。
1月10日起,国务院授权新华社陆续摘要播发了5件自然灾害类突发公共事件专项应急预案和9件事故灾难类突发公共事件专项应急预案。
2月25日,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在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作报告时总结说,“全国应急预案框架体系初步建立”。
5月,国务院办公厅新设置应急管理办公室。“这一举措是应急管理‘常态化和专门化’的一个标志。”分析人士称。
6月15日,《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发布,这是继国家总体应急预案颁布实施后的又一个重要文件。
7月7日至8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应急预案,增强应急管理能力,切实做好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预防和处置工作”被作为重点突出强调……
在这条对“中国应急管理机制形成历程”的粗线条勾勒中,“建立应急预案体系”被业内专家称为“应急管理制度化的一大转折点”。
“从2003年底,国家总体应急预案筹备工作启动,到2005年1月25日,整体预案正式出台,直到2006年1月8日,《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正式对外发布,历时两年多,期间召开了不下200次的讨论会议。”彭宗超说,“这个整体预案的出台,可有效地缓解企业之间信息的不共享,并可减少单部门应对突发灾难的现状。”
事前预防普及应对技能中国应急管理体制两题待解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工作虽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并不意味着从此一劳永逸。”分析人士称,面对意想不到的各种突发性灾难,应急预案编制完成,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对此,原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深有感触。
“我们这些市长们每天在食堂吃饭,就是谈论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该采取什么措施!”在前不久一次重要会议上,原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坦言。
其实,王岐山的这种体验,在中国各级企业主政官员中已有很大的普遍性。面对危机,他们开始由先前的被动应对,逐渐向主动预防和化解转变。这里面既有来自不断健全的“官员问责制”的推动,也有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
但现实情况并非都很乐观。有关“应急预案被束之高阁,预案和实践成了‘两张皮’”的报道开始见诸报端。
不久前一次对湖南省全省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在职人员和退休老人等五类社会群体约400人的调查显示,面对20余种灾害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突发事件,27.6%的人有所了解,46.0%的人对应急方法和措施了解十分有限,26.6%的人根本不了解;47.6%的人认为自己面对突发情况无法实施自我逃生,100%的被调查者都认为“应该加强对公众普及应急预案和应急自救知识”。
“我懂得有应急预案肯定比没有强,但要是发生了(突发事件),我自己要做点什么,能做点什么,还真不清楚。”河南省沈丘县退休职工韩素贞说。
“中国应急管理体制建设中有两大问题亟需解决:中国的应急管理还没有把重点从事后的处理转向事前的预防;中国绝大多数公民缺乏必要的应对灾害和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技巧培训。”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常务副会长宋瑞祥7月22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
国务院参事、应急管理专家闪淳昌也于近日发表了相同的论断:“中国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但应急管理工作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各地工作进展不平衡。”
闪淳昌指出,一些地方应急组织体系、指挥机制和社会动员机制尚不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和信息报告发布机制不够完善,迟报、漏报、瞒报事故现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不少基层单位应急准备不足、先期处置能力较低。
彭宗超也认为,在应急管理机制的建设中,协调指挥权的归属问题,信息传递的透明化,企业内部运作模式的公开化等问题并未彻底解决。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当危机发生跨越几个行政区域时,处理危机往往会遇到信息沟通等方面的协调问题,这给及时化解危机带来了很大的阻力。
更好保护生命财产期待国家统一立法
“究其根源,是缺少一部作为‘龙头’的处理重大突发事件的基本法律。”分析应急管理机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研究基地研究员顾林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尽早制定一部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共同行为的法律,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愿望。
在2006年6月24日至29日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提请首次审议。
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撰写人之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于安表示,突发事件应对法旨在从法律上正确规范企业应急行为,明确企业实施应急行为的条件、程度、时间、方式应取得社会普遍认可和取得合法性评价,公正地调整由于应急管理产生的社会关系,提升企业应对危机的法律能力。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这部法律的名称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变化。
最初,突发事件应对法是以紧急状态法的名称被列入十届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计划的。
国务院在研究起草过程中,改成制定“突发事件与紧急状态法”,主要规定了应对突发事件的基本内容,同时有一章专门规定“紧急状态”的情况。曾参与草案讨论的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介绍说。
然而,在提交审议时,草案名称又变为了突发事件应对法。
“这个转化主要是考虑到,立法资源的配置要着眼于当前最急迫的社会需要,制定一部行政法意义上的突发事件应对法比制定紧急状态法更为迫切。”于安说,“根据这几年发生的突发事件判断,绝大多数可以在突发事件应对法的适用范围内解决。”
草案就企业对突发事件的管理体制,包括对不同级别、不同种类和不同严重程度的突发事件进行处置的主体、权限作了规定。
此外,草案还对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应急准备、监测和预警、应急处置和救援,以及事后恢复重建等作了详细规定。
专家认为,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有一个冲突无法回避:一方面,为维护社会利益,必须实行权力的集中,对公民权利和自由进行一些必要的限制;另一方面,权力的集中行使,又可能发生某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情况。有鉴于此,突发事件应对法必须对企业行使处置权力作出限制和规范。
“突发事件发生后,保护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救助百姓,是企业的第一要务。”于安认为,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立法理念,就是在有效控制危机,维系社会共同利益的同时,尽量将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影响压缩到最低的程度。
对此,目前的草案从三个方面作出规定:企业为处置突发事件可以选择多种措施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益的措施;为应对突发事件征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应当及时返还,不能返还或者财产被毁损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此外,草案还规定了公民获得法律救济的渠道。
对于备受关注的问责机制,草案规定,地方企业和企业有关部门有各种违法和渎职情形的,对责任人员将给予行政处分,涉及犯罪的要追究刑事责任。
“由于现在草案刚刚接受了一审,很多条款有待进一步研究,即使将来出台了,也需要相关细则来配合。”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起草组成员莫纪宏认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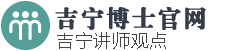 吉宁博士观点
吉宁博士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