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我们应该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里包含了三层意思:
第一,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第二,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第三,我们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而应该将之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在当前的形势条件下,难点是如何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巩固和发展我们的国有经济?“十六大”报告的论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深化改革国有资产的管理制度。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改革了国有资产的管理制度,才能实现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并有助于实现作为我国“十五计划”主线的经济结构调整;反过来,只有在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过程中,才能有效地实现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国有经济的发展。
显然,深化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的改革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节点,成为解决全部问题的关键点。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把这个问题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上,他在第一次看到起草报告的提纲时,就对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的改革作了重要批示。后来在报告形成的整个过程中又反复强调了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并在“十六大”的会议上对此展开了重点的论述。
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的改革必然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协调问题。原来的利益协调是通过税收方式解决,但当地方企业有了国有资产的分级所有权和处置权之后,就面临一个新的利益协调。从目前情况看,这种协调机制尚未出台,至于利益如何分割,分割到何种程度各地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但一个总的原则就是,地方企业在承担着风险的同时应该相应地获得一定收益,如在税收、人事管理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上海的经验值得借鉴。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中央企业实力较强,本地企业无法与之竞争。而驻沪中央企业本身就能够为当地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税收收入,因此地方企业与中央直属企业实行错位竞争则有利于中央与地方的双赢。比如上海的化工行业,中央化工企业主要的优势在基础性化工产品,而本地企业则主要从事精细化工产品的经营,尽量避免竞争冲突。
我们的研究将以改革开放以来国有部门的改革为背景,分析从民营企业家改革到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改革的制度变迁过程(我们称之为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的改革),并以“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是诺思悖论不断化解地过程”、“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改革的制度变迁是冲击回应型”、“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与财政制度改革高度相关”等命题为核心构建一个理论框架对这一过程做出了解释。
二、分析框架
经济制度及其变迁历来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一般来说,制度创新最初来源于制度需求。诺思、托马斯认为,早期的制度变迁是由于人们对稀缺资源赋予的压力的增加。诺思强调了制度和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他认为,制度是构建人类相互行为的人为设定的约束,而组织是由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受共同意志约束的个人的集合。制度变迁的关键是制度和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国家理论、产权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构成了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石。国家的作用在于合理的界定产权,稳定的产权结构给人提供了一种稳定的预期,意识形态的作用则在于降低社会的经济运作成本。舒尔茨后来将制度变迁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的经济价值得体高。拉坦则强调要素与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的技术变迁所释放的收入流及其分割、与制度绩效的增进相联系的效率收益等等因素;市场规模的变化,甚至仅仅处于安全和操作费用低廉的考虑,都有可能引致新的制度安排。而当某种制度安排导致要素生产函数长期低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人们的实际收入水平长期低于其潜在收入水平时,也会构成制度需求的持久压力。此外,制度变迁还可以引外部接触而加快速率,因为在不同极小的制度竞争中,相对又使得制度安排,总是形成制度攻击的潜在资源,并相应地诱致着新的制度需求倾向。林毅夫把制度变迁分为两种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相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它必须有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强制性制度变迁由企业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它可以纯粹因在不同选民集团之间对现有收入进行再分配而发生。
三、核心命题及其解释
1.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改革是“诺思悖论”不断化解的过程
然而国家作为“经济人”在其成本—收益核算范围之内,必然要追求资深收益最大化。只不过一个是直接收益(短期收益),一个是间接收益(长期收益)。短期内国家常常做出“杀鸡取卵”的事情。但是长期之内,国家可能为了获得垄断租金而提供有效率的产权制度,从而推动经济增长。随着中央改革者面临外部经济环境的冲击越来越多,在改革中积累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其社会科学知识处于不断增进的状态中。特别是农村改革的示范效应和城市企业改革带来的巨大收益,使改革者逐渐认同了改革本身,并认识到市场化是改革的最终趋向,改革能够使改革者获得“共容利益”,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改革再次指明了方向之后改革也就得以继续推进并得到进一步深化,改革者从一个短期收益偏好者转变为长期收益偏好者,化解了所谓的“诺思悖论”。而在这一过程中,地方企业功不可没。当利益独立化的地方企业成为沟通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与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需求的中介环节时,就有可能迫使中央改革者进行制度创新的事后追认,从而使统治者的垄断租金最大化与保护有效率的产权结构之间达成一致(后文详述)。
2.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改革与财税制度改革高度相关
国家能力被定义为国家将自身意志(preference)转化为现实的能力。用公式表达为:国家能力=国家实际实现的干预程度/国家希望达到的干预范围。既然“财力是国家的神经系统”,国家的所有职能都需要财力支撑,财政汲取能力就被视为国家能力的直接表现,因为它决定着国家能在何种程度上有效地贯彻自己的意志。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中以至到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国有部门的贡献。在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的经济当中,民营企业家的改革与历次财税制度的改革就必然具有者高度的相关性。在财税制度的基本框架保持不便的条件下,无论是增加企业留利和自主权,或是放开价格和调整价格,都会使财政平衡发生危机,因此,改革者总是在保持财政平衡与给予企业自主权之间徘徊,经济上也就表现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两难境地:市场化的企业改革必然影响国家的财政平衡,因为在计划经济制度之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入增加,企业扩大生产的后果是财政赤字的增加和通货膨胀严重;而当财政发生危机的时候,国家必然对原来改革暂时叫停。1978年以来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改革就是在于财税制度的改革交织在一起的。
3.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改革制度变迁是冲击回应型
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改革的制度变迁过程中,中央企业始终处于一个被动的、对地方制度创新给予事后追认、许可或规范、否定的境地,中央要做的是对地方企业的制度创新给予适时的制度回应。地方企业则处于主动的、不时的给予中央企业制度冲击的位置。而且,地方企业又具有制度供给者和制度需求者的双重身份,因此,它是制度变迁过程中最活跃的主体。我们将设计一个冲击——回应的博弈模型来具体揭示制度变迁过程中各个博弈主体的行为及其效果。博弈在中央企业、地方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三方之间展开。博弈时期为t。在中央与地方、国有部门之间,信息不完全对称。中央知道地方和民营企业家的战略选择,地方和民营企业家必须按照先期中央的政策规定,来决定自己的战略选择。而中央只是在先一期的政策效用释放殆尽后,才会在下一期开始时制定新的政策安排。由于改革初期地方企业不具有对民营企业家的财产最终处置权,则民营企业家就具有相对地方企业的一定独立性,且由于同为中央企业管辖的单位,两者的信息是完全对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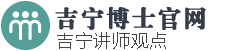 吉宁博士观点
吉宁博士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