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哲学,本着“一以贯之”的包容性,站在生命的立场来看中国管理哲学。宇宙之间,共同存有无数生命。集体在动变,个体亦在动变。一经“行”动,难免有所冲突。如何才能各得其所“天地位焉”?各遂其生“万物育焉”?必须各别依据“管理之道”自动调整,以期共生、共存、共进化。这种中国管理哲学,乃是永恒不变的。从开天辟地,一直到天地毁灭。中间既不死亡,也不衰落。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道没有定形,也没有固定的所在,所以是佛家所说的离言说相,不可以用言语来表示。但是智能极高的人,观察它的深远与空虚。根据它普遍而循环的运行,勉强用言语、文字来加以描述,这就产生了中国管理哲学。
中国管理哲学,是整个生命哲学的一部份。主要的课题,仍然是生命。它以生命为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和安顿我们的生命。中国管理哲学的道理,即在彰明自身所本有的灵明德性,再推己及人,使人人都能够除去旧染之污而安居乐业,并且尽心尽力做好自己份内的工作。大家都站在最合适的立场而彼此密切配合,用择善固执的态度来取得最适当的协调。大学说得十分明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因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种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的“一贯的道理”,这样精微开展的中国管理哲学,包容了中外一切管理思想。兹为方便说明起见,爰就管理的意义、目的及方法,分别叙述其包容性如后:
(一)、管理的意义,即是“修己安人的历程”。
中国管理哲学,首先重德。认为经理人,必须对道德具有清楚的观念。因为德性是操之在我的,我欲仁斯仁至矣!管理的知识并不是不重要,而是既多又杂,永远学不完。庄子说:“我们的生命是有限度的,而智识是没有限度的。以有限度的生命,去追求没有限度的知识,就会弄得疲困不堪!”经理人无法学得所有的管理哲学知识,势必拿所学到的一部份知识,把它强调得无以复加,认为再好不过,形成“天下的人各执一端以自耀”。于是“X理论”(TheoryX)、“Y理论”(Theoryy)、“Z理论”(TheoryZ)纷纷出笼;“企业文化”(CorporateCultures)刚刚肯定“英雄人物是公司最重要的要素”,指出“英雄主义是被现代化管理里乱所遗忘的领导要项。”“追求卓越的管理”(ManagingforExcellence)马上描述“管理人员由于英雄作风只能达到平凡的绩效”,因而推出“超英雄领导模式”(Postheroicleadershipmodel),要求领导者不要像“城边奇侠”那样殚精竭虑,靠一己之力承担一切。学生产的强调生产管理的重要性;学市场的认为时代已经迈入市场导向;学会计的闷声不响把预算控制捧得高高在上。墨子说:“一个人有一种道理,十个就有十种道理。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道理,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道理,等到人数多得数不清,那么他们所说的道理,也就多得数不清了。”
探讨管理智识如此麻烦、复杂,倒不如提升层次,从德性的修养入手,反而简易、可靠得多。经理人凭良心,依照意志的自律而行,那么所当行的是什么?何者应当请教专家?如何才能诚以致曲?怎样达成最适的决策?这是很容易明白的,平常人都可以做到。
经理人重视“修己”,中庸说:“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力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生知安行的人,先天的要件已足,只要“自诚明”,就原有的德性加以扩充,由“慎独”、“温故”的工夫,以“敦厚”的修养,便能达于广大高明的境界。至于学知利行或困知勉强而行的人,天资虽嫌不足,也可以“自明诚”,一方面多多向他人请教而“知新”;一方面抱“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弗能弗措”的决心以“崇礼”,只要遵道而行,不半途而废,亦可到达“明”与“强”的地步。修己包含问学的功夫,却特别注重“诚之”的修养,亦即“择善而固执”。
中庸以为“诚”是有诸中必形诸外的,经理人诚于中即能表现于外,形于外就能更加显著,因此格外光辉发越,足以感动人心。追随者一旦发生感应,便容易产生变异,与经理人同化。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即是由经理人一端的“诚”而引起追随者感“化”的过程。孟子说:“人能充满不欲害人的心,那仁就用不完了。人能充满不做窃盗的心,那义就用不完了。”经理人充满仁、义的心,便可以由一端的诚扩充到全体,结合众人的部份智识,明辨而笃行之。
如果经理人不从修己着眼,却要依照意志的他律而行,那么他所需要的智识,很显然是不足的。就算他肯处处虚心请教专家,也需要用智能来判断、取舍和决定。经理人绝非万能,怎么能够以自己拥有的一些知识,来判断追随者的智识呢?有时反而“气死专家”,岂非冤哉枉也?西洋经理人多半重视追随者的“工作能力”(Can)与“工作意愿”(Will),就没有想到不诚的人,其能力愈强、意愿愈高,后果将愈不堪设想!我国经理人大多注意追随者的“忠诚”与“肯干”,而两者都与个人的“修己”密切相关,愈忠诚愈肯干的人,愈重视修己,则其效果必然愈为良好。
经理人修己、正己,又何以保证追随者必定也修己、正己,并且好好地尽一己之心,尽一己之力为组织目标而奋斗呢?这就有赖于“安人”。特别是中国人十分考究心安则为之,追随者果能安居乐业而又身安心乐,没有不克尽职责,忠心耿耿的。
中国管理哲学是修己安人的历程,包容了知和德,而以德性为优先。智识可以利人,亦可以害人;德性则只能利人,不能够害人。经理人必须以德控知,用德性来判断智识,才能把握生命的可贵,而不致残生害性。
(二)、管理的最终目的,即在安人。
中国管理哲学在古代就已经初步形成。一次,孟子对齐宣王说:“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他主张施行仁政,无非为了安天下的百姓。荀子疆国篇说:“故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也明白地表示人生的根本要求在“安”。荀子最重视礼义,把它当做修身治国的最高准则,但他却说“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可以启发我们体认礼义的功用,亦无非在实现人生的安宁。孔子思想以道德哲学为基本,而儒效篇说:“言道德之求,不下于安存”,“安存”实际上即等于孔子所主张的“安百姓”。道德所求的,不外乎安存,正表示了道德的任务,就在于实现人生的安宁。
道德哲学适用于管理上,在中国便是中国管理哲学。孔子的中国管理哲学:,实际为其中国管理哲学的延伸。他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管理应该“以德”,最好“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使组织成员,都能够“有耻且格”。“格”就是“正”的意思,孔子的中国管理哲学,以“正”为起点,任何组织,首先应该建立制度,以调整上下成员的权利与义务,以求“正名”,做到“君君,臣臣”。但是,孔子如果仅止于此一阶段,则不过是封建的后卫,未必遽能获得“贤于尧舜”的地位。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对于那些“德所不能化,礼所不能治”的少数人,我们固然不得不动用刑罚,遏止其所恶,以维持团体的秩序。我们也应该觉察这样刑罚的结果,虽然得以暂时抑制恶行而茍免于罪,却依然不知羞耻,恶行难免乘机窃发。因此不废刑罚,只能算是正名的治标工具,必须进一步提倡化导,以使成员悦服。孔子理想中的管理,乃是“近者悦,远者来”的境界,组织成员都能够“既来之,则安之”,获得他们心目中所向往的安宁。安宁之后自然喜悦,所以孔子中国管理哲学,以“安人”为管理的最终目的。
企业管理如果强调“利润”,不妨问以“假若利润带来不安,还敢要吗?”行政管理通常标榜“绩效”,亦可测以“若是绩效甚高,而后果十分不安,又将如何?”恐怕答案都是否定的。人生的根本要求是安宁,管理自须以安人为其最终目的,一切分目标无不包容在内。
(三)、管理的方法是“经权”。
全世界的管理,事实上都离不开“经权”,但都没有儒家说得那么清楚而透彻。“经”即“常道”,为“不易”的原则,现在叫做“共识”。“权”是“权宜应变”,为“变易”的措施,通常叫做“变通”,含有“越变越通”的意思。管理的对象,无论五M(人力─Manpower、财力─Money、机械─Machine、方法─Method、物料─Material)、七M(加上市场─Market、士气─Morale)或者十M(再加上管理信息─ManagementInformation、管理哲学─ManagementPhilosophy、及管理环境─ManagementEnvironment),都随着时、空在变动,经理人必须随机应变,以求制宜。但是漫无目标地变动,或者一味求新求变,很容易走入“为变而变”的歧途,往往变而不能通,甚至越变越不通,反而失去“变通”的本意。这时“共识”的建立,也就是变动原则的确定,便成为当务之急,惟有彼此把握“不易”的共同准则,朝向既定的目标,才能越变越通。
制度化是管理必经的过程,却不是良善的管理。任何制度,即使十分适合外在的需要与内在的用意,也不可能绝对有利而无弊。一切遵照制度办理,势难因应两可或例外事宜,同时行之日久,也不免官僚、僵化。管理确“立”制度之后,必须再赋予适当的弹性,这就是“权”。荀子不茍篇说:“欲恶取舍之权,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计之。”“权”的意思,是详察事情的利害,审慎比较以定取舍,亦即衡定可否,以求权变能得其宜。
不错,变迁是不可否认,也不容忽视的事实,求新求变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活动。但是,那些没有时间性与不可更改的价值观念,同样也是不可否认也不容忽视的事实。在中国管理哲学中,中国经理人应该“有所变,有所不变”,秉持孔子提示的原则:“义之与比。”一切取舍,都应该决定在“义”。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那些应该变?那些则不应该变?“义”就是衡量的最高目标。朱子注释说:“可与权,谓能全轻重使合义也。”“权”可以说是中国管理哲学的“合理化”,因为“义”者“宜”也,便是“合理”。
近世经理人,深受达尔文(Darwin)进化论的影响,几乎只知有变,而不知有常。因而重视“变的法则”,却严重地忽略了“不变法则”。经理人如果一方面强调“制度化”,一方面又力主“求新求变”,不免形成以制度管理员工,而经理人自己则拥有充分的自由来求新求变。假若如此,岂非口口声声“法治”,最后都变成“人治”了?
“权”在“求新求变”之外,还应该“义”之与比,亦即所有“新”的改“变”,都必须合“义”。“一切权宜应变都应该合义”,这是不易的常道,我们称之为“经”。“义”则是随应变迁,没有定型,必须要用知虑来决定的。经理人在应变的时候,不能够像循礼那样,只要依照成规去行,所以“权”比“立”难。管理合理化,事实上要比管理制度化,更高一层次。
孔子把人分成中人以上、中人和中人以下三种,中山先生称之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等人,希望他们分知合行。组织成员,如果各自依“义”权变,由于彼此标准不一,知识程度不同,思虑判断的结果也不一样,难免纷乱不堪。所以上级交付下来的“经”,即是下级应该遵循的“义”,明白规定只可依此权宜应变,不可擅自改“经”变“义”。当然,上级的经必须光明正大而又公正无私,因此管理的先决条件是“修己”。上级的经,有赖于下级真诚秉持着去做适当的权变,所以管理的最终目的在“安人”。部属得安,就会相信上级的“经”,才会真心诚意地去调整应变。
“经权”的“经”,即易经中的“不易”;“经权”的“权”,系易经中的“变易”。儒家宣导“持经达权”,使中国五千年来,从容融合外来文物而仍能中道。更成为中国人长久以来,共同沿用的管理方法。
经理人一本“经权”,便能做到朱子所说:“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即无一事之不合理,故于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也。”经理人确立若干管理信念,并且坚持“权不舍本”(亦即“权不离经”)、“权不损人”、“权不多用”的原则,同时“经”的订定,以安人为导向,建立“权是为了经的达成”的共识,那么所有的管理工具与方法,俱可放心运用了。
大学首章,朱子称之为“经”,实乃世界上最为完备,至有系统的管理哲学,是经理人所应具有的共识。它不但是“初学入德之门”,而且是“经理人必有的理念”。
大学之道,讲求的是解决重大问题所应当采取的途径,是垂百千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决策理论,更是包容了所有中国管理哲学的真理。
大学三纲领,指出经理人必先修己,以相亲相爱的方式来关怀所属,亲近追随者,并且采取适时适切,至佳至当的立场(止于至善)。这三个纲领相互关连,其义一贯。“在明明德”系经理人表现公正、开明的态度,以身作则,来获得部属的向心和信心。“在亲民”是经理人主动亲爱、亲近追随者,重视双向沟通,使管理更为有效。这两个纲领相互推进,才能达到第三纲领“在止于至善”,凡事无不合理,而后成员安之怀之,即能“安人”。
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经理人从“格物”开始,彻底把事物的道理研究清楚,到了真正有所认识,并非一知半解,便是“致知”;所知既然透彻,则信之笃,执之固,同时既不欺人,亦不自欺,即已“诚意”;既信之笃,执之固,则心无旁骛,志归于一,而无所偏倚,便能“正心”;心是身的主宰,心正则言行随之俱正,这样就叫做“修身”。以上五端,都是“成己”的功夫。经理人真正关爱追随者,必须切实从“成己”做起,因为“成己,仁也”,惟仁者爱人必以其道,才能使追随者亦有所成立。所以中庸说:“成物,知也。”经理人具备相当的智识,才能逐步由“齐家”、“立业”、“治国”、“平天下”以“成物”。
但是,这些“得之于外”的智识,必须有赖“发之自内”的智能,来加以判断和运用,“合内外之道”,才能够管理得恰到好处,获得“时措之宜”。可见中国管理哲学,包容“德”“知”。三纲领和八条目,也涵盖了中外一切管理的道理。
经理人茍能以大学之道为“经”,把它当做不易的管理原则,那么劳伦斯‧米勒(Lawrence Miller)在“美国企业精神”(American Spirit)一书导研中的感叹:“在寻求新管理做法的狂热中,所缺的是检讨管理灵魂与精神,也就是管理阶层是依据何种基础而有管理的权力。”即能获得彻底的解决,因为经理人只要“权不离经”,尽管依据三纲领、八条目去权宜应变,都可以找到最适决策而止于至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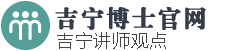 吉宁博士观点
吉宁博士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