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在他那本发人深省的自传《旁观者的冒险》中曾这样写道:“我和其他维也纳的小孩一样,都是胡佛总统救活的。他推动成立的救济组织,提供学校每天一顿午餐。这顿午餐的菜式,清一色是麦片粥与可可粉冲泡的饮料,直到今天我仍然对这两样东西倒胃口。不过整个欧洲大陆,当然也包括我在内的数百万饥饿孩童的性命,都是这个组织救活的。”一个“组织”居然能发挥这么大的功用!从德鲁克活生生的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德鲁克强调“透过组织这种工具,尽量发挥人类创造力”观念的根源。
吉姆·科林斯在《基业长青》一书中写道:“我们发现,我们的研究和德鲁克的著作深深契合。事实上,我们对德鲁克的先见之明深为敬佩。研读他的经典之作,像1946年出版的《公司的概念》、1954年出版的《管理的实践》和1964年出版的《成果管理》,你会深深叹服他遥遥领先于今日管理思潮的程度。”为什么德鲁克能走在管理学的前面?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德鲁克研究的不是管理学。
尽管德鲁克以“现代管理学之父”的称号而闻名,但是几乎看不到德鲁克用管理学大师的名号自称,在他赋予自己的“头衔”之中,包括:教师、作家、咨询业者等等,唯独没有管理学家。对于德鲁克而言,管理学是工具,是技术,是他研究的问题的解答与实践,但不是他研究的问题本身。
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德鲁克,怀有一种“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研究的目的是“如何创造一个能运行的**”。他观察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是一个多元的**,所有的**任务被交付给各种大型的组织……”那么,德鲁克研究的问题在这种前提下就具体为“如何创造一个有效的组织或机构”。而对这个问题以及由其衍生出来的问题的解答,就构成了德鲁克的管理学,或者可以说,管理学是德鲁克研究的“副产品”。
正是如此,德鲁克和其他的管理学家有了显著的区别:如果说古典管理学派的泰罗试图用科学实验方法将管理提升到科学层次,法约尔用职能理论使管理具有了一般的意义,韦伯对普遍性原理的追求企图将管理提升到理性层次,那么是德鲁克通过对人类**中管理作用的重新理解,—将管理提升到崇高层次。他唤醒了管理界,使人们认识到管理对于人本身生存和发展的重大价值和意义。
人本主义的管理学家
泰罗及其追随者们认为管理学是一门科学,但是德鲁克认为管理学是“从经济学、心理学、数学、*理论,历史和哲学中汲取营养的学科,简而言之,管理学是一门人文学科”。这正如德鲁克自己坦承的:“从我写第一本书开始至今,我所写的一切无不强调人的多变、多元,以及独特之处。”
德鲁克的研究很少使用数学模型,这一点颇受诟病,也是他游离于主流管理学之外的主要原因。不过,这并非是因为德鲁克不懂数学,而是德鲁克发现在研究管理问题之时,数学难有用武之地。德鲁克承认自己在20岁时写过两篇计量经济学方面的文章,“精深”得令人难以忍受,他评价那两篇文章:“错得十分离谱,在数学应用方面无懈可击,结论却是愚蠢之至。”在德鲁克眼中,管理的本质是在于对人的复杂性的高度关注,而人的行为和动机是无法模型化的,或者说将人模型化是对人的价值与尊严的降低。
事实上,德鲁克管理学说的最大危机反而是来自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批评。
德鲁克认为“有经理观念的责任员工和自行管理的工厂是我最重要和最有创意的思想,也是我所做出的最大贡献”。不过,马斯洛认为德鲁克在这个问题上过于理想化了,“他轻视了选择合适的个体来实现他的管理原则的必要性;另一个是他忽视了邪恶的存在,病态的存在,还有一些人身上普遍的恶劣性的存在。”在马斯洛看来,德鲁克的管理原则“可能起作用的只是那些相对健康的人、相对坚强的人、相对优雅和善良的人,有德行的人”。“如果我们有一些进化良好的人类能够成长,并且很急切地要求成长,那么在这样的地方,彼得?德鲁克的管理原理就好像很不错。这些原理是有用处的,可是,也只能在人类发展的顶层才有效。”
对于马斯洛的批评,德鲁克并没有回复,但是在他的自传《旁观者》一书之中有一段为弗洛伊德辩护的话可以作为他对马斯洛的回应:“我认为,真实的弗洛伊德要比传统述思中的弗洛伊德,要来得有趣得多。他实在比寻常人复杂—他自己就是一名悲剧英雄。尽管弗洛伊德的理论实在是薄弱,他企图把笛卡儿的理性世界与灵魂的黑暗世界合而为一,并故意忽略所有不利的问题,然而,终究会支撑不住。但我还是要说,这样的理论仍然非常迷人,透露不少玄机,而且深深地触动人性。”
彼得·德鲁克通过对通用汽车历时18个月的调查研究,在1945年出版《公司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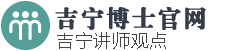 吉宁博士观点
吉宁博士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