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90年代,华尔街投资银行摩根大通(JP Morgan)的一支年轻团队设计了一种新的营利方式信用衍生品。仅在十年之内,这些新奇证券的市场就膨胀到12万亿美元以上—-一些人将全球金融危机归咎于此。的吉莲•邰蒂(Gillian Tett)新近出版了,在这本书中两段摘录的第一段中,她揭示了这个革新性的妖魔如何从瓶中被放出来—-令它的创造者大为恐慌的是,它最终毁坏了这个系统。
摩根大通的银行家们设计的创新信用衍生打包产品可能存在的一个结构性问题在1998年下半年初现端倪。在此之前的几个月,摩根大通信用衍生品团队的核心成员布莱斯•马斯特斯(Blythe Masters)和比尔•德姆查克(Bill Demchak)就一直在游说金融监管机构。他们认为通过使用这些他们帮助创设的新型信用衍生品,摩根大通可以更好地控制其向公司所提供贷款组合的风险,从而减少必须用于担保可能的违约行为的资本金额,问题在于削减的幅度有多大。(虽然这些信用衍生打包产品之后被冠以其他名称,例如担保债务凭证(CDO),当时这些创新型结构被称为“小酒馆”(Bistro)交易,即Broad Index Secured Trust Offering的简称。马斯特斯和德姆查克代表自家银行进行了最初几笔小酒馆交易,他们当时对问题的答案并不明确。但当他们为其他银行进行这些交易时,资本准备金的问题变得更加重要—-其他银行主要对削减准备金要求感兴趣。
金融监管机构对这种做法不甚确定。美国货币监理署(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以及美联储(Federal Reserve)最初得知信用衍生品和担保债务凭证时,他们对于银行试图控制风险的想法表示支持,但他们也感到不安,因为新的衍生产品不大符合现行法规。另外,对于用极小数额的资本来担保衍生产品的损失,他们对此尤其拿不准。
当这个团队进行第一笔小酒馆交易时,他们集中了300多笔摩根大通的贷款,总价值97亿美元,并根据这些贷款的收入流发行了证券。这种想法的吸引力显而易见:根据他们的计算,只需拿出7亿美元—-一笔相当小的金额—-来担保300多笔贷款的违约风险。经过激烈的辩论,信用评级机构对团队的风险评估表示赞成,但如果金融灾难导致7亿美元完全损失,额外的损失必须由摩根大通自己承担。对马斯特斯和德姆查克而言,出现7亿美元亏损的机率非常小。
欧洲监管机构不赞同这种做法,一些美国的监管官员也对此深感不安。纽约联储第一副主席克里斯汀•卡明(Christine Cumming)向马斯特斯和德姆查克指出,如果摩根大通想获得减少资本准备金的许可的话,这家银行应该寻找一种为其余风险(他们最初的小酒馆计划中“缺失的”90亿美元)保险的方法。因此马斯特斯和她的团队开始寻找解决方案。他们先是为“未保险的”风险打包产品起名。马斯特斯喜欢将它称作“比AAA级更胜一筹”,因为它被认为比AAA级证券还要安全。但这个名称在市场上不适用,因此他们将其命名为“超高级”。接下来就是寻找愿意购买这一产品或为之提供保险的公司。
这项任务似乎并不轻松。对摩根大通而言,这种风险产品其实根本不存在风险,因此只需支付象征性的金额为其投保。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想要购买超高级风险打包产品或为其提供保险的人都必须有足够的勇气踏入这个完全陌生的领域。
AIG毁灭之源
马斯特斯最终找到了超高级风险产品所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曾经是与摩根大通长期合作的蓝筹客户之一。和摩根大通一样,AIG是美国金融业的支柱企业之一,它因20世纪初期在亚洲市场建立起庞大的特许经营而声名鹊起。之后AIG的业务范围扩展到美国,成为二战后美国经济的强大臂助。人们认为AIG是一家完全值得信赖的大公司。与摩根大通一样,AIG也拥有AAA信用评级。
但在AIG内部,企业子公司正在蓬勃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AIG雇佣了一批之前就职于德崇证券公司(Drexel Burnham Lambert)的交易员。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德崇证券是垃圾债券之王,由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领导,现在这家公司已不复存在。这些交易员建立了名为AIG Financial Products的资本市场公司,公司设在监管体制较为宽松的伦敦。这家公司由约瑟夫•卡萨诺(Joseph Cassano)掌权,他是一位布鲁克林出生、精明强干的交易员。卡萨诺极富创新精神、勇敢并且雄心勃勃。更重要的是,他知道作为一家保险公司,AIG不像银行一样受到资金准备金方面累赘规则的限制。这意味着它只须留出非常小的一部分资金—-如果它为超高级风险产品保险的话。另外,这家保险公司也不大可能面临其监管机构的诘问,因为AIG Financial Products是监管机构的漏网之鱼。这家公司主要由美国储蓄机构监理局(US Office for Thrift Supervision)监管,而该机构的官员在这些前沿金融产品领域的专业知识匮乏。
马斯特斯向卡萨诺提议由AIG为摩根大通的超高级风险产品作担保,卡萨诺欣然同意。卡萨诺之后评论说,这是个“分水岭式”事件。他解释说:“摩根大通找到我们,我们同他们有过很多合作,请我们参加其所谓的小酒馆交易,这些交易就是担保债务凭证(CDO)市场的前身。”对AIG而言这似乎是个不错的生意。
AIG从其提供的这项服务中获得相对较少的一部分利润—-承保的每一美元每年的收益仅0.02美分。但如果0.02美分乘以数十亿倍,就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来源,特别是如果不需要准备金来覆盖风险的话。神奇的信用衍生产品再次提供了“双赢的”解决方案。很多年后人们才发现,正是卡萨诺的交易使AIG走上毁灭之路。
与AIG达成交易后,摩根大通团队向监管机构指出已经找到解除小酒馆交易其余信贷风险的方法。他们开始计划向其他保险和再保险公司出售超高级风险,保险公司大力抢购,它们不仅从摩根大通购买,也从其他银行购买。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这一业务开始突飞猛进时,美国监管机构再度插手。美国货币监理署以及美联储向摩根大通指出,经过审慎的考虑他们认为银行无需将超高级风险从账面转移。马斯特斯以及其他人的游说似乎起了作用。监管机构不愿让银行如此轻易取得成功。如果他们在账簿中保留超高级的风险,他们就必须按通常金额的1/5保留准备金(8%的20%,这意味着账面上每100美元的准备金为1.60美元)。另外还有一些条款。如果银行能够证明交易的超高级部分的违约风险确实可以忽略不计,并且通过小酒馆模式发行的证券具有从“国家认可的信贷评级机构”获得的AAA信用评级,它们才能按这种方式削减资本准备金。这些条款非常严格,但摩根大通愿意遵守。
这造成巨大的影响。银行被迫为每100亿美元的公司贷款在账面上保留8亿美元的准备金。目前这一数字可能降低到1.6亿美元。小酒馆概念与国际银行业规则终于达成一致。
有一段时间,德姆查克的团队停止从摩根大通转让超高级风险。当时德姆查克对事情的进展感到极为不安。超高级风险快速膨胀,增长到惊人的数字,因为当银行为客户安排这些信用衍生品交易时,它实际上将交易的超高级风险放到了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从理论上看没有需要担心的理由。但到1999年,期货交易的总金额膨胀到1000亿美元。巨大的风险开始违背德姆查克的常识。他对他的团队说:“如果你的资产负债表上有600亿美元、1000亿或者不管多少亿美元,这都是个非常大的数字,我不认为你应该忽视这样巨大的金额,不管它到底是多少亿。”
相关性问题
德姆查克准确地意识到,为信用衍生品交易中涉及的风险建模有其局限性。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是围绕着“相关性”的问题,即任何特定贷款池中的违约可能的相关程度。试图预测关联性有点像计算一个袋子里有多少苹果会烂掉。如果你花几个礼拜观察几百个不同的没有联系的苹果身上会发生什么,你可能会猜一个苹果会烂掉-或一个也不会烂。但是如果它们都是在一个袋子里的呢?如果一个苹果开始烂了,是不是其他的也会烂呢?如果是,有多少会烂,会烂得多快呢?
类似的猜测也遍布在企业界。摩根大通的统计专家认识到,公司债务的违约是相关的。如果一家汽车公司开始拖欠债务,其供应商可能也会跟着破产。相反地,如果一个大型零售商倒下了,其他零售集团可能会受益。相关性可以有两面性,而要计算出它们是怎样在任何一揽子公司里的发展是极为复杂的。所以统计专家所做的,基本上就是研究过去在公司违约和股价的相关性,并编程设计出模型来推定当前相同模式下的情况。这种假设被认为不是特别冒险的,因为公司违约是少数,至少在摩根大通研究的公司池中是这样。比如,当穆迪为在第一笔小酒馆交易中的一篮子公司完成其自己的建模时,它预言每年只有0.82%的公司会违约。如果这些违约是不相关的,或者只有一点点相关,那么公司池中10%—-这个数字可能会吞噬筹集的7亿美元资本来弥补损失—-发生违约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这就是为什么摩根大通可以宣称超高风险是如此安全,这也是为什么穆迪把那么多此类证券评定为AAA级。
然而事实是,关于相关性的假定只是:猜测。而且,德姆查克和他的同事们完全知道,如果相关性比率在现实中比统计专家假定的高一点点,就会导致严重的损失。如果出现众多公司随着一些公司的违约而违约的情况呢?要引发这样一个连锁反应的违约数量是个让人恼火的未知数。这德姆查克从未见过此事发生,而且这个可能性似乎已经持续了极其长的时间,但是即使只有一丝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他可不想看到自己坐在1000亿美元注定要破产的资产上。所以他决定要安全地做,并且不顾管理层说什么,他告诉他的团队要寻找方法来进一步减少他们的超高责任。
这个立场花去了摩根大通相当可观的资金,因为它不得不出钱来为超高风险向AIG和其他公司进行保险,且这些费用十年来稳步上升。在AIG的第一笔此类交易中,保险费率仅为每年0.02美分/美元。到1999年,价格就接近于0.11美分/美元。但是德姆查克坚决认为,他的团队必须要审慎。
抵押的定时炸弹
与此同时,这个摩根大通的团队在第二个可能更大的问题上绊住了。由于创新周期的轮换和来自早期基于公司贷款池的小酒馆交易收入的下降,德姆查克要求其团队探索小酒馆类型交易的新用途,或者通过修改结构或者通过在混合中注入新型贷款或其他财产。他们决定以抵押做试验。特瑞•杜洪(Terri Duhon)是这次尝试的核心人物。十年前,杜哈恩还只是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名高中生。当她告诉她的亲戚她将来要在银行工作时,他们只是认为她会在银行做个出纳。现在她掌管着数百亿美元。她被培养成了一位数学家,业余时间她喜欢竞技运动和骑摩托车。尽管如此,她发现掌管这么大笔钱才是激动人心的。“这是种非常特别、非常紧张的经历”,她后来回忆说。
杜洪上任一年后,她得到消息,一家德国大银行Bayerische Landesbank想要用信用衍生品结构来消除其已发放的140亿美元抵押贷款的风险。她和她的团队讨论是否接受这项工作;跟抵押债务打交道不是摩根大通的惯常举动。但是杜洪得知,银行的一些竞争对手已经开始进行抵押风险信用衍生品交易,所以他们的团队决定接受这项工作。
杜洪跟定量分析师一谈就碰到了问题。摩根大通在1997年末提供第一单小酒馆交易时,它获得了所有它汇集起来的贷款的大规模数据。自从银行有意公布了所有有贷款的307家公司名称开始,购买应运而生的信用衍生品的投资者也同样可以得到数据。另外,许多此类公司已经做了几十年的生意,所以可以得到许多数据,看到他们各个商业周期中的表现。这给了摩根大通的统计专家以及投资者以巨大的信心来预测违约的可能性。但是抵押的情况就不同了。首先,当银行向外部投资者出售一组抵押贷款时,他们几乎从不披露个别借款人的名称和信贷记录。更糟糕的是,当杜洪开始寻找数据跟踪几个商业周期的抵押违约时,她发现数据很少。
当美国的企业界在20世纪后半段遭遇数次兴衰之时,住宅市场却一直稳步攀升。某些地区遭遇了市场滑坡: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末储贷危机中德克萨斯州的房产价格下跌。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再也没有一次全国范围的房价下跌。事实上最后一次全国房价大规模下跌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缺少数据使得杜洪非常紧张。银行经理整合模型来预测违约既需要有繁荣时期也需要有萧条时期通常发生的数据。没有数据,就不可能知道违约是否有相关性、在什么情况下违约是独立发生于特定的城市中心或区域、什么时候违约会遍布全国。杜洪找不到任何方法来得到抵押贷款的这些资料。这意味着她只能依赖于仅仅一个地区的数据来推断整个美国的情况,或者就违约是怎样相关的做出比通常更多的假定。她与克里斯那•瓦利库提(Krishna Varikooty)及其他定量专家讨论该怎么办。瓦利库提以冷静面对风险而出名。他讲究细节,而他的这种谨小慎微有时会得罪那些急于完成交易的同事。但是德姆查克总是为瓦利库提说话。后者对抵押债务的判断非常清晰:他没有信心找到任何追踪潜在违约相关性的方法。他宣称,没有数据,根本不能在抵押池中对违约风险做出精确评估。如果抵押的违约是没有相关性的,则小酒馆结构对于违约风险来说是安全的,但是如果它们高度相关,那么就可能会有灾难性的危险。没有人能知道。
杜洪和她的同事们不愿意就这样回绝Bayerische Landesbank的要求。甚至在被告知建模的不确定性之后,这家德国银行还是非常希望可以继续。所以杜洪做出了她可以做出的最好的评估来设计交易的结构。为了解决不确定性,她的团队在合同中保证要筹集大于普通规模的防范性资金,而这使得摩根大通这单交易的获利减少。银行也避免了它的风险。这是唯一能采取的谨慎防范措施了,杜洪是不会再做这种交易了。抵押风险实在无从得知。“我们没办法舒坦下来”,马斯特斯后来说。
几个月后,杜洪从小道听说其他银行开始做抵押债务信用衍生品交易,她很奇怪,他们是怎样解决让她和瓦利库提如此担心的数据缺乏的问题的。他们是不是找到了更好的方法来追踪相关性问题?他们是不是在抵押交易上更有经验?她无从知晓。因为信用衍生品市场是不受监管的,她看不到交易细节。
摩根大通团队只在几个月后又做过一次抵押债务的小酒馆交易,价值100亿每元。然后,随着其他银行加强了他们的抵押支持业务,摩根大通基本上就出局了。八年后,曾令杜洪、瓦利库提和摩根大通团队畏惧的无法量化的抵押风险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它遍布于欧美世界的财务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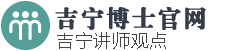 吉宁博士观点
吉宁博士观点
